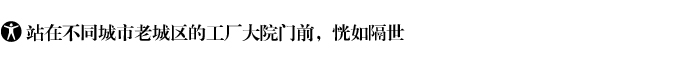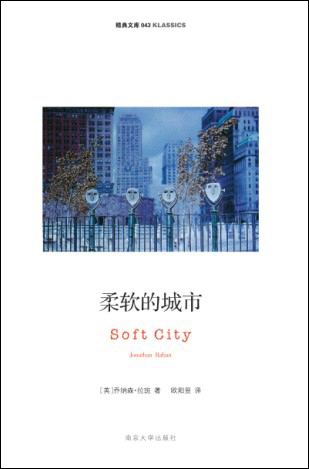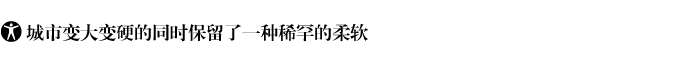|
|
|||||||||||||||||||||||||||||||||||||||||||||||||||||||||||||||||||||||||||||||||||||||||||||||||||||||||||
 我出生于鄉村,可是對城市中的工廠大院卻有著極為熟悉的親切感。按照我的理解,城市工廠大院是一種基于傳統的家庭生活形態,就像在鄉村生活的人們出門不遠處就是土地,在工廠大院生活的人們出了家門就是車間。 特定的年代,工廠是土地的變形體,除了缺少鄉村土地的大量土壤,工廠大院的結構與鄉村形態無異,它延續的仍然是鄉村土地的生產模式。不僅如此,工廠大院里人與人的交往、感情也與鄉村人情往來并無不同。 并且,城市工廠大院與鄉村更為一致的地方在于方向感的弱化、空間感的強化。所以,即使熟悉工廠大院的生活場景,到了不同工廠大院的門前,還是會出現對空間的不適應,哪怕它的前后左右都是再熟悉不過的街道和坐標。 這種體驗與鄉村鄰里間的相處幾乎是一樣的,雖然能夠看到屋前屋后的炊煙,但是走到鄉鄰門前的時候,依舊是浮生夢醒的陌生空間感。 |
||||||||||||||||||||||||||||||||||||||||||||||||||||||||||||||||||||||||||||||||||||||||||||||||||||||||||||
 出于生存的本能,在陌生的城市最容易發現這座城市和出生地、生長地的相同相似之處,因為不同顯而易見,而相同的細微卻依靠內心捕捉。這不僅是落腳不同城市的感覺,也是在同一座城市內部還能夠勉強區分城市不同區域、不同生活結構之美的關鍵。 黃萬松先生是地道的上海人,他從上海來到青島,參與這座城市的房地產開發。在一次帶有顛簸感的午餐中,我問他對青島的適應程度,他告訴我"很容易,因為青島和上海很像。" 當然,他所說的青島和上海這兩座城市相像的部分并非在于城市的文化結構和建筑結構,而是曾經有一段時間,青島和上海都是工業(工廠)城市,尤其是 "上(海)青(島)天(津)"并稱三大紡織工業基地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 一定程度上,過去城市工廠大院完成的是現在城市郊區的功能——為城市發展提供支持的同時,也拓展了自身空間的功能、完成了自身功能的生活實踐。然而,最大的不同是,城市工廠大院對空間界線有著明確的要求,以現在的標準看,城市工廠大院讓完全不相識的人形成團體緊密且排他的社區價值是不可思議的。即便到了現在的城市社區,因房地產開發而形成的社區重點也只是排他,聚集到社區內的居民再也無法形成過去城市工廠大院的價值體系。 不過,現在的城市工廠大多數都轉移到了城市開發區,尤其是汽車工業和互聯網產業幾乎擠入城市每一個角落的病毒式發展,城市的生活形態改變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