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乡村:从被动走向主动

这是2024年5月19日在新西兰剑桥小镇拍摄的秋日景色
文/胡凌啸
编辑/马琼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乡村则蕴藏着滋养文明发展的土壤。由于在二者关系中城市处于强势和主导地位,乡村特质的延续和变迁深受城市影响。城乡关系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城市繁荣伴随着乡村的衰败,不仅乡村特质受到破坏,而且阻滞乡村发展,并最终影响到城市。
近些年来,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逐渐被世界各国接受和推广,重要的一条就是促进城乡平衡发展,保护乡村特色风貌。
城乡融合发展绝不是要按照城市的样子去打造乡村,让城乡同质化既不现实,也不科学,而根本目的是让乡村居民也能够过上与城镇居民同等品质的生活。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城乡融合发展本身就有缩小城乡差距之内涵。
在发展中消除城乡差距
相关分析指出,只有在达到相对较高的发展门槛时,一个国家内部的城乡生活水平才会趋同。城乡差距问题是在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也要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解决。
当今的高收入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也曾面临着很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例如,在19世纪瑞典和芬兰,城市地区的成年男性人均财富分别比农村地区高出200%和150%;英国的城市工资比农村工资高出70%以上;城乡工资差距在澳大利亚、丹麦、法国、日本、美国也都超过50%。
但在20世纪中后期,这些国家陆续通过完成工业化实现了城乡均衡,为“在发展中消除城乡差距”提供了证据。
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日本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乡村则出现人口老龄化、过疏化,村落数量减少,经济活动萎缩等衰落迹象。1960年代农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城市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大约少30%,城乡矛盾日益突出。
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投资增加,建筑业、运输业和公共服务业等行业在全日本范围普遍发展,农民获得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同时伴随道路交通网的建设和家用汽车、摩托车的普及,农民选择非农就业的地理半径得以扩大,到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居民收入中有80%以上来自农业之外,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甚至比城镇居民高出16%。
政策干预不可或缺
在发展中消除城乡差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府的政策干预可以缩短这个过程的周期。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科学恰当的政策干预不可或缺。
作为后发经济体,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缩小与先发国家的差距,普遍采取了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对农业农村进行更为严格的控制,城乡差距因此被进一步拉大。如果没有针对性的政策干预,很难完全依靠经济发展本身来扭转城乡失衡的不利局面。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如何以富有效率的发展方式向更加城市化的经济过渡,同时以富有公平导向的政策干预平抑城乡差距。
从先发国家的经验看,往往都是在工业化的中期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并根据本国实际不断对政策进行阶段性调整。总体来说,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认识相关政策——一种政策并不直接以缩小城乡差距为目标,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但最终发挥了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的作用;另一种政策则直指城乡差距,聚焦农村发展,有的甚至上升为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如韩国的“新村运动”、德国的“村庄更新计划”、法国的“乡村整治计划”等。
先发国家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正面素材,而拉美、非洲一些国家的发展也提供了教训,政策干预失当或者缺乏有效干预都可能会加剧城乡差距。
比如,尽管拉美地区的巴西城市化率达到88%,阿根廷超过90%,但由于在城市化过程中盲目扩大城市外延,造成失地农民持续增加,城乡社会严重割裂。贫民窟规模十分庞大,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41%的农村居民是贫困人口,19.5%的农村居民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乡村发展,化被动为主动
现代社会,有形的道路、无形的互联网等基础设施无限延展,覆盖城乡所有角落,也让城乡边界日益变得模糊,城乡之间的相互影响继续加深,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乡村面临来自城市的全方位嵌入、渗透,更容易让其陷入乡村特质消失、发展停滞、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困境。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扭转乡村这种被发展、被改变、被塑造的被动局面,努力形成将乡村特质转化为发展优势的体制机制,帮助乡村化被动为主动。
一是挖掘乡村多元价值。乡村的经济活动并非只是农业生产,从乡村自身的多功能性出发可以有着更为丰富的选择。例如,德国在政策上支持打造多功能农业和多功能乡村,支持保护乡村景观文化,促进“半农业”和旅游业、手工业发展,为乡村人口充分就业和增收提供稳定保障。
二是引导城市产业向乡村转移。把城市产业引导到乡村发展是一些国家激活乡村经济的重要方式。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东部工业城市和西部农业乡村在收入、公共服务等方面差距悬殊,分别呈现了一个富裕的工业法国和一个贫穷的农业法国。
为缩小城乡差距,法国实施了“领土整治计划”,其中“工业分散政策”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该政策旨在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事业,限制人口和工业在巴黎、里昂、马赛等区域过度集中,鼓励企业向乡村地区迁移和投资。
同时,法国创建了“区城自然公园”作为承接城乡经济往来的平台,通过乡村高品质的自然景观吸纳各类城市经济活动来此举办,旨在实现自然景观与人文活动的互补互进”。
三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偏向农村。为缩小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各国都注重把公共设施建设资金更多地用于农村。
例如,20世纪60年代,德国出现的“逆城市化”进程推动德国开展村庄更新工作,主要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更新,同时对乡村自然环境进行保护,财政资金对村庄更新中的历史建筑修缮保护发挥着主导作用,各级财政承担了80%的修缮保护费用,还承担了个人住房改造费用的20%,让各地乡村能够体现各自的别致景观。
在人类文明存续层面上,乡村所特有的自然生态、文化习俗、建筑风格、生活方式等,都极为珍贵且不可或缺。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人们都不应丢弃蕴藏于乡土社会之中的丰富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而应共同守护这份宝贵的乡土遗产,让人类文明在多元与和谐中永续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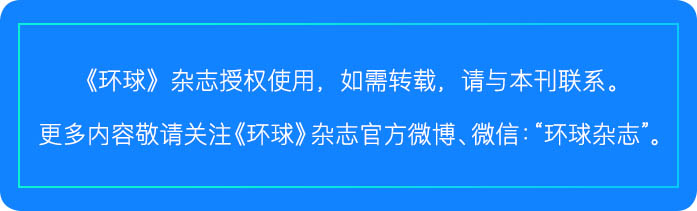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